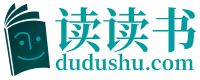小心火车!
我是在这样的警告里长大的。在道口、扳道房,以及靠着铁路的墙上随处可见。有时是圆圆的警示牌,有时是用石灰水刷的歪歪扭扭的字迹,更多的是呵斥或叮咛。
到了奶奶嘴上,就是唠叨了。奶奶能把学龄前儿童都认识的四个字,演义成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,悲壮的或凄惨的,然后,她警觉地抬头侧耳,捕捉着隐隐约约的汽笛声。
住在铁路边,每天有几十成百对列车打窗下通过,她对汽笛却仍然敏感。在悠长或急促的汽笛声中,她总会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儿,惶惶不安地凝视飘散于远天的煤烟。灾祸的消息传播得风快,一时半会,整个铁路新村都朝着报警的尾笛狂奔,挣出怀的奶子和扶摇于风中的白发,孩子和冲在他们前面的狗,咬着他们裤脚的鹅。其中少不了奶奶那拳头般的小脚。无论汽笛是否属人身事故,是否与自己的亲人有关,所有的心都在路上狂奔或张望,那场面很像暴雨之前的蚁阵,浩浩荡荡却又慌慌张张。
今天我为之感动的,却是少年的我所无法理解的。也许,汽笛长鸣,只是为倒在轮下的扒车的流浪汉或捡煤核的老太婆致哀,但即便是平凡的生命,也把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惊醒了,并为之掩面而泣或扼腕长叹。
不会是对火车的警惕和敬畏浸透血液,成了集体无意识吧?
长鸣的汽笛的确是恐怖的。偶有事故发生,随着报警的呼号,东边的调车场,西边的客站,北边的江边货场,所有的机车都拉响了尾笛。此伏彼起,如惊涛拍岸,乌云压城。凶讯是漫空飘洒的煤灰,把所有的脸色都熏黑了。
仔细看,奶奶白净的脸上还有六十年前的烟灰残存在皱褶里。她丈夫是火车司机,驾着车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游击队的导火索上往来穿梭。终于有一天汽笛为他长鸣。我能想象出灾难的现场,被炸的火车冲出轨道一头栽到桥下,车头砸在干涸的河床上引起锅炉爆炸,列车垂挂着像一条被击中七寸又砸碎了脑袋的黑蟒,满地是钢铁的碎片和火焰,满地是血肉和煤炭。
而唠叨的奶奶几乎从不向我们描述与自己有关的那场灾难的细节。即使回答邻居的再三追问,她反复陈述的也只是自己在事故前的预感。我隐约得知,那天本该她丈夫歇班,因为当班的同事病了,他自告奋勇替班出车去。丈夫出门之后,她坐在门口纳鞋底,不祥之兆在穿针引线时接踵而至。那天的针锥很不好使,一再断针;那天的顶针极不安分,一不留神就挣脱手指蹦到地上;那天的麻绳锋利如刃,勒得她掌上一道道血痕。更出奇的是,丈夫忽然打门前一闪而过,诧异间她紧追出门,却见一马平川的远方黑烟如柱,腾空而起,漫卷残霞。接着,就是凄厉的尾笛声裹胁着她,裹胁着所有人,朝车站狂奔。
每当这时,她的表情很奇怪,没有悲伤,没有冤屈和悔恨,仿佛那些情感已被岁月稀释了,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命运之谜,对那个谜的恐惧、疑惑和执着的探究。
不该他的!那死鬼不是存心撇下我和孩子吗?你说说。她恨恨地问邻居。
可能就为了破解内心深处的疑惑,她守着青春岁月,寡居在浓黑的烟云和洁白的汽雾里,在机车卸下的煤渣堆里翻寻着煤核和命运的谜底。靠着拾得的煤核,她拉扯大两个孩子;而扑朔迷离的悬念融化成了泪光闪烁的叮咛:小心火车!
我记得曾有两次,我临时被老师或同学带去看演出,来不及告知家中。那两个夜晚奶奶寻遍了车站、道口、调车场,叩问了煤台、水鹤、三角线,却偏偏忽略了学校和灯火辉煌的铁路俱乐部。她呼喊着我的名字,用尾笛一般惊心的声音。
一场演出的时间可以想象,我回家并不算晚。然而,第二天所有的目光都在追问我,指责我。他们说:你这孩子真是!你奶奶杵着小脚,黑灯瞎火到处找你,摔着怎么办!
在警告和叮咛中长大的子弟中学的学生,仍然无法抵御火车的巨大诱惑。那铿锵有力的出发,那风驰电掣的到达,调车员手里的信号旗,守车上车长的大檐帽,如同童话中的小木屋一般的扳道房,甚至火车头有意吓唬孩子而猛然放汽,都能唤起我们亲近火车的念头。
可能老人们至今还不知道,初中三年,男孩子们上学放学大多是以车代步的。出入库的机车便是接送我们的校车。那些火车头恰好要到铁路新村附近换道,我们躲过所有的警告和司机的注意,像那些警示一样,牢牢地贴在火车头的前面和后面。站在前面的排障器上,感觉最为心惊肉跳,人像一块落入轨道中的石头被巨大的力量推着奔走,脚离迅速卷入轮下的钢轨很近,就在一个闪失之间,而风一直在狠狠地碾着身体。
在江南最大的编组站上,有时,我们也扒从驼峰上下来的溜放车,依偎着东北红松、烟台苹果、高坑煤炭和南来北往的粮食、化肥及其他。车轮碾压着安放在钢轨上的铁鞋,发出刺耳的尖叫,在不绝于耳的尖叫声中,我们快活得身心发抖。
我在轨道上疾驶。一个疾驶的人是不会在意路边的警示乃至风景的,眼里只有前方,前方便是呼啸的风,鼓荡在胸怀里。
现在回忆儿时有些后怕,而那时我们庆幸从未被家长发现,甚至得意忘形。仿佛是挑战警告,我们在调车场上放声歌唱,股道间供作业用的麦克风把歌声扩大了许多倍,那反叛的歌声笼罩了整个城市。
可是,在经历了下乡插队之后,有两位儿时玩伴却一不小心撞响了汽笛。一位顶替父亲做了司机,丧身于该他驾驭的机车轮下;膂力过人的线路工的儿子,则失去了双臂。
我能想象他们入路时的激动。
我家老三几乎和他们同时成为铁路工人。老三做了调车员,是铁路上最危险的工种,成天随着溜放车跃上跳下,摘钩解挂,撂闸制动。我家大门对着车站单身宿舍,那里有位轧断双腿的调车员。许多年来,先是拄双拐拖假肢,后是摇着轮椅,在我们眼皮下进进出出。少年时在澡堂里遇见他,我总是紧盯着,看他怎样脱衣怎样入水怎样上岸,尤其对腿的断面充满了好奇,但我从来没有看清。一个光溜溜的人总有办法遮掩住自己的断面,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。
从老三上班的第一天起,全家人的心就被悬挂在调车场上空的烟云和轰鸣中了。每天,送他出门是千叮咛万嘱咐,盼他下班的心情精细到了读秒,秒针就是他回家的身影,他行走在焦虑的时间上。每逢雨雪天气,更是叫人成天忐忑不安。而他总是满不在乎,乐乐呵呵,来去蹦蹦跳跳的。
没几年,他居然当师傅带徒弟了。那阵子,他在梦里都美滋滋的。母亲在半夜里听到他自豪的宣告和爽朗的笑声,第二天笑话他,他满脸绯红地赖账。我便挺身而出加以证明。我也听到了。我觉得他的梦境里一定有酒,有一帮小伙子,在觥筹交错间他高声宣布:我当师傅啦!或者,是雄赳赳地站在溜放车上,呼唤着徒弟的名字。
老三应该知道当师傅意味着什么。七十年代,就在那条铁道线上,出过一位英雄。列车行驶在雨季里,他发现前面塌方,却刹不住车了,他逼着他的徒弟——副司机和司炉跳车,而自己陪伴着他的机车他的职守一道钻进泥石流。他的事迹曾经家喻户晓,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。如果没有别的原因,我想这也很自然,在蒸汽机时代,这样的故事并不稀罕,另一个故事会风驰电掣地驶来。
三班倒的调车员每十天一个大休。带着徒弟的老三似乎从没大休过。该他大休时,都去替班了,他给家里的解释是想攒下足够的休息日到福州、杭州玩一趟,却多少年未成行。他的豪爽、仗义,让我相信,他的血脉里更多地承继了祖辈的气质,我知道他替人当班多半是见人有困难主动提出的。而他竟忽视了奶奶的眼睛。
那苍凉的叩问在她眼里闪耀了多半个世纪!
我没有机会成为铁路工人,尽管我从小渴望着,甚至认为命定了。我想,假如我是,我也会像老三一样,以出色的技术驯服那钢铁的猛兽,以身轻如燕的姿态舒展自己;也会用笑声去瓦解家人的担心,随便撒个谎,躲过奶奶对延时到家的追究;也会对为难着的同事慷慨地擂响胸脯;走吧,有我呢。
这是火车教的。蒸汽机车出发前蓄足气力的长嘶、通过时那一日千里的狂傲,到达时那余威犹在的得意的喘气,都会叫人莫名地亢奋起来。我多次搭乘过货物列车的守车,还在火车头上跑了一程。在炉膛打开、司炉甩开膀子往里投煤的瞬间,那么近的距离和那么猛烈的动作,令我心里一惊:他不会用力过猛把自己给投进去吧?虽是一个闪念,却极有可能窥破某些牺牲的内在秘密。我固执地相信,在蒸汽机时代,有些英雄就是被炉火点燃激情,被汽笛惊醒勇气。
比如,我的一位邻居。他勇斗歹徒牺牲在站台上,成为一尊英武的铜像,如今已锈迹斑斑。而在民间传说中他的形象依然锃明剔透,邻居道着他的小名笑他的木讷、较真,又为他当时缺乏机智唏嘘长叹。因冲动而勇猛,为激情所献身,这难道不是流淌在平民血液中的,最质朴因而最具亲和力的英雄气质?
我家老三肯定也经常面对险情。我只发现了一次,在手上,是个淤黑的指甲帽。他来不及藏了。他一直搪塞,实在逃不出追问,才披露真实的原因:当溜放车从驼峰上冲下来,他手里的叉竿怎么也叉不住铁鞋,情急之下,他扔掉工具,徒手抓起铁鞋,俯身塞向隆隆驶来的车轮。被征服的车辆发出钢铁的尖叫。我在这样的尖叫声中长大,我能体验征服者的心情。老三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面对我,说着说着,就王婆卖瓜了,炫耀自己的技术和灵巧。要不是我厉声警告,他可能会兜出深藏在心里的更为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平安的祈愿拒绝那些故事。我知道,倾听就是激励。我学会了警告和叮咛,以奶奶的口吻,以整个铁路新村的表情。
一位老师傅曾向我展示过他的身体。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,尽是疤痕。戳伤、砸伤、烧伤、炸伤,遍体伤痕以至于层层叠叠。那是触目惊心的履历,又是耐人寻味的线索。我一一探访了它们的来历,和抢时间争速度的新线工程有关,和他巡守的每个日子有关,也和他急躁火爆的性格有关。所以,我笑着说:你是个容易受伤的男人。他眼一瞪:抢修线路是掐着点的,急了,我恨不得举镐在自己脚背上扎个窟窿,不给自己放点血,还叫身先士卒,还能调度现场的紧张气氛?
我无意取笑被汽笛煽动的激情,即便那激情极可能酿成了某些无谓的牺牲。恰恰相反,当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女声女气的风笛取代了蒸汽机车奔放的汽笛,我怀念已经逝去的阳刚气十足的日子,怀念为火车沸腾的热血,为火车牵挂的心,生命与钢铁的缠绵,激情与速度的比拼。
现在,我家依然住在铁路边,却听不到列车通过的动静了。窗不响,地不颤,人也再不可能依靠客车的到发来报时。电力机车牵引的列车悄悄地去来,虚幻如不觉间流逝的日子。
平静让人麻木。
奶奶是在家中去世的,为她守灵的那两天,我们总觉得在掩面的白布下面有一种声音,像吞咽,像叹息,更像卡在嗓子眼里的叮咛。一次次揭开白布,只见她面容安详。但其中有一次,我看见她眼角有泪。我不禁失声,安息的生命居然也会流泪!
我轻轻为她抹去。我的手指被灵魂的泪水濡湿了。
奶奶葬在调车场南边的山林里。为她下葬那天,我发现满山的墓碑有许多我熟悉的姓名。几乎都是铁路职工和家属,是铁路新村的邻居。那些名字老了。那些名字曾经英俊如路徽,有着火车头的轮廓和心情;曾经坚韧如“干打垒”的平房甚至工棚,随时等着为新线开通而迁徙,不觉间竟矗立了一生;曾经鲜嫩如列车员从外地捎来并分发给邻居的时令蔬菜,西红柿或青辣椒;曾经旺盛如哺乳期的乳房,坦然而神圣地面对众多目光,把奶水响亮地射入搪瓷茶缸,端去喂养出乘职工的儿女,溢出来的乳汁润湿了烤在茶缸上的关于纪念安全日的文字。
我把那座坟山称之为“铁路二村”。那些灵魂来自五湖四海,那里的风操着南腔北调。由他们的乡音,我大致能准确地判断他们的工种。比如,湖南人多为大修段的线路工,本地人以车辆段和货场居多,车站的调度员十之八九是江浙人,所以列车不管停靠在哪儿,都能听到喇叭里江浙味很浓的铁路腔。
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片山林。正如他们不约而同地去车站接车,接从各自故乡捎来的信息,那信息是天津麻花山东大葱福建荔枝广西砧板以及其他;正如他们不约而同地涌向长鸣的汽笛,或扛着扫雪工具涌向被大雪覆盖的车站。尽管当地政府作出殡葬管理规定,不允许在此处安葬。他们还是以迁回老家的名义,取出骨灰,和铁路新村的老邻居做伴来了。枕着调车场上的钢铁轰鸣,庇佑着他们的子孙。
小心火车的警告是严厉的,而在以火车为象征的命运力量面前,它有时又是非常虚弱的。在这座山上,便有永不瞑目的灵魂,我听到他们的泣诉和低语了。
先是一个苍老的男声。他是马上就要退休的扳道员,小儿子将顶替他的岗位,在外地工作的儿女特意赶回来庆贺,为他举行最后的晚餐。他用叮咛和一生的经验灌醉了小儿子,而自己饮的是行车规章,是一种叫忠于职守的果汁。可是,在亮如白昼的调车场上他居然受惊了,僵立于道心仰天长嘶,像一匹让人联想起某位英雄的烈马,最后一个晚班是无情撞向他的溜放车。
再是一个妙龄的女声。身为列车员,她是旅客违禁携带易燃易爆品的受害者。猝不及防的爆炸,甚至不允许她留下最后的惊呼或沉吟,她的死成了宣传乘车安全须知的生动事例,被广泛援引,我在许多趟列车上的广播里都听到了她的名字。那名字在广播里活了七八年。七八年间她的许多同事做了母亲。
我还能想象她的模样。她是哥哥甩不脱的尾巴,是家长们的密探,是警告的执行者,因而是一群去扒火车的男孩子的仇敌。最幸福的仇敌。男孩子用在铁道边捡来的糖衣笼络她,用在道口路灯下捉的“土狗子”贿赂她养的鸭子,用扒车去沿线农村采的桑叶拉拢她喂的蚕宝宝。
我记得她喂的一团箕蚕,怎么也不肯在她准备的箩筐里结茧,满世界爬了去。从她家涌出来,在大门洞、在楼梯口、在相邻的我家,天花板上、墙旮旯里,到处吐丝张网。尤其她家里,头上、身边尽是编织的奇丽景象,一团团,一簇簇,洁白似雪,晶莹如梦。
如果用调车场来比喻,丝网就是银光闪闪的轨道,茧子就是错落其间的扳道房;如果用车站调度室里的运行图来比喻,已结成的茧子就是车站,正忙着选址的蚕宝宝就是运行着的列车了。
我猛然一闪念:现在长眠在“铁路二村”的他们是蛹了,把自己藏在各自的情思里、牵挂里,欢乐和痛苦里,藏在蒸汽机时代的精神内部、记忆深处,他们会羽化吗?
2002年——2004年初稿
2009年7月10日——2010年3月19日重写
2010年5月10日——2010年6月30日再改